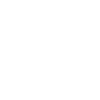一日忽发奇想,“沭”之名字由何而来?,它为何叫“沭”,而不是其它?“沭河”名字之前是否还有其它的称呼?可否在古典文献中追寻一些蛛丝马迹,为家乡母亲河增添一些文化底蕴呢?
网络上的常识性解释是:五代时期的文字学家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说:“邑中道而术,大道之派也。”“术(术)”字的本义是道路,“沭水”之名应该与道路有关。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记述:春秋时期,我国东部有一条南北交通要道,这条道路北至齐国都城临淄(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南至徐国(江苏省泗洪县附近),中间经穆陵关、莒国(今山东莒县)、郯国(今山东郯城县北)。由于这条道路“僻在东方”,其重要性略逊于中原地区的主要道路。只能算作是一条主干道中的分支。这个观点与徐锴所说“大道之派”相符,因此可以将这条道路称为“术道”。而从沭河的流经地域看,“术道”与“沭水”二者路线一致,相依相傍,古人便把这条“僻在东方”的交通要道一侧的河流称为“术水”。“术水”成为这条河流的名字后,古人为了区别字义,又在“术”字上加了“水”旁,即“术”,《汉语大字典》注:“术,同'沭’,水名。
从这个解释来看,明显的是后人推测前人的定义命名,用后世之学术附会前世之说法,这是一种因果颠倒的逻辑思维,似乎并不令人信服!
再说,这条辟在“东方”的交通要道,并不一定是“僻”道,说不定,这条大道开辟之时,中原还不一定有能称得上“大道”的道路可谈。
现根据新的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成果,将平时搜集的资料稍做整理,对“沭河”之称谓做进一步的探究,以期与共同爱好者们交流分享和研讨。
一、茅河之谓
常在老家街头闲聊,有时聊起沭河轶事,老人们不时以“茅河”代称,对于将沭河称之为“茅河”,这是久居沭河岸边人们的俗称,对此早已习以为常,通常的说法是大河两岸盛长一种又硬又长、耐风吹雨淋日晒的茅草,这种草本植物在农村用处很大,晒干后可以搭建如茅草屋、茅草亭子、猪栏屋子等一切遮风避雨的建筑物。不认识这种草的人们可以通过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句体会它的用途。查阅地图,至今莒县境内沭河的一条支流仍标注为“茅河”,因沭河茅草而起名的村庄有河东区沭河西岸的大、小茅茨村,郯城县茅茨庄和前茅茨村,这种原生态的名字,既是原始状态下人们“逐水草而居”法则的有力证明,也可能是原始先民们最早选择沭河岸边而居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竟它有着天然的原始建筑材料可满足先民们搭棚建屋的需求。这个名字可能是沭河最原始、最早、也是叫的时间最长的名字。
由此联想,沭河除民间的“茅河”这种原生态纯天然叫法之外,是否还有藏于古典文献里的人文雅称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东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沂蒙山区和鲁东海滨,尤为重要的是1981年9月“沂源猿人”头盖骨和7枚牙齿化石的发现。其表现出来的性状特征与北京猿人、安徽和县猿人接近,处于直立人阶段。1982年5月为配合兖石铁路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在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工地发现700余件细石器,这是山东地区首个被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其与苏北大贤庄遗址、桃花涧遗址、爪墩遗址等石器面貌非常接近,从而引发了关于“凤凰岭文化”等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此后鲁南苏北常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学者分析研究。山东地区尤其是沂沭河流域成为探讨华北细石器技术出现、传播与扩散的重要区域之一。沂沭河流域也奠定了其在山东地区旧石器工作最为厚重的工作、研究基础。
河流是文明的载体。旧石器时代晚期,沂源猿人逐水而居,南下定居于沂沭河冲积平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开始了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的原始农业活动。沂沭河流域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考古工作者在北起沂源、沂水,中到莒县,南至郯城县的沂沭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先后发现“细石器文化”遗存地点上百处,均为1~2万年前的人类所创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大墓45座,出土文物3000余件,其中有大口尊、漏缸、高领罐等,部分大口尊腹部刻有疑似“日月山”图符,专家学者们纷纷对这些图符进行研究,认为这是我国汉字的雏形,并对图符进行释读,虽未形成一致的释文,但都认为:“陵阳河墓地前后三次发掘45座大汶口文化墓葬,就时代而言皆属大汶口文化晚期。”
1973年,诸城市前寨村发现许多陶器。1980年秋,经过考古发掘,清理了近百座大汶口、龙山文化墓葬,特别是陶尊残片刻有“日月山”残字,与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一模一样。经专家研究,诸城前寨遗址与莒县陵阳河遗址属同一部族遗址。
山东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刻有“日月山”图符的大口尊
这些遗存主要集中在沭河流域,它们是哪个部落遗留下的?史学界的说法不一。有专家认为,这一部族文化遗存应是有虞氏部落遗址。主持莒县陵阳河与大朱村大汶囗文化墓地考古发掘工作的王树明先生在《仓颉作书与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尊文字》一文中指出:“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遗址考古发掘,两地发现的物质文化面貌完全相同,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完全一致。因而又推定,莒县陵阳河一带发现的陶尊文字,也是帝舜太昊部族的物质文化遗存。”
这是新石器时代沂沭河流域,尤其是沭河流域先民们创造古代文明的有力物证,沭河流域是中国文字的发源地,著名的大汶口和东夷文化主要发祥地。在此基础之上,“沭河”名称也迎来了由自然到人文的新变化。
二、“江”之称呼
将沭河称之为“江”,以时间顺序,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卷 4《东山经》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注:这里的“泰山”指“沂山”,远古时期山东境内称泰山的还有几处,现在的泰山最初反而叫“岱山”或“岱宗”,见下图),故《水经注·沭水》记载:“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大弁山与小泰山连麓而异名也。”《山海经·东山经》所记诸山,基本上在今山东省境,这是前人一致的看法,沂山也称泰山,同样是共识。
其次,《史记》卷 3《殷本纪.汤诰》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这里的商朝以前的先民们所记古“四渎”之“江”,怎么说都不会是今天的“长江”,而应是在淮水东北方,即今鲁南、苏北地区的一条较大河流。在这里,较著名的水道是发源于鲁中山区的沂河 (旧称沂水 )和发源于沂山山脉的沭河 (旧称沭水 )。据《水经注》卷 25 泗水篇及沂水篇末以及卷 26沭水篇所记,此二水在古代都在下邳城 (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州城 )附近入古泗水,更东南流,于今江苏清江市 (旧淮阴县 )以北入淮水,东流入海。这条古沭水同上述“四渎”之“江”的位置基本相符。
有的专家学者也认同这里的“江”是鲁南苏北的一条大河,但将其定位于“沂河”,这是地理方位和地缘政治的误判所致,沂沭两条大河同时形成于一亿三千多万年前的中生代晚期,且沭河位在沂河东边,是沂沭河谷(或沂沭走廊)的东界,无视地理位置而降将西界沂河称“东”,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从古代边缘地理政治角度看,沭河河谷是东部沿海地区由鲁南苏北平原出入山东半岛胶莱平原的唯一通道,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南上北下的必争之地,战略地位非同一般,地缘界限非常明显。上文说道,傍沭河而行的东方大道不一定是“僻道”,这条大道的开辟可能远远早于中原,理由就在于此。而沂河上游直插蒙山深处,地缘界限并不清晰。
沂沭河谷地缘政治图
再次,《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
同时,《史记》卷 30《平准书》在记载:“是时(指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
由此也可看出:直到汉武帝时,“四渎”之“江”也还不是指长江,而是与其他三渎“咸在山东”。
综上所述,可知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到《封禅书》所记“咸在山东”的早期“四渎”,应是反映着当时以邹、鲁、泗上(今山东省中南部)和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随后的“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古代“山东”居民的主要水道知识。江、淮、河、济分据东南西北的方位,就是围绕着这一地区而定下的。后来(大致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长江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于是长江就取代了沭河而成为“四渎”之一,并反映在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中。日久之后,《山海经》所记“江”、《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中关于“四渎”的最古记载、《封禅书》所引汉初人“四渎咸在山东”的说法等等,反而被看成不可理解,从而很少被人提及了。
认字知史,古代有句话叫作“不认字,不知史”,中国文字渊远流长,象形、会意、形声、指事是其主要特点,书体衍变历史久长,从汉字的特点和演变中,可读懂很多历史常识。具体到沭河之“江”的名字,可从以下“工”“江”两个汉字着手解读。
关于“工”与“江”,《山海经·海内经》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其中提到“共工降生江水和治理江水”的史实,与沭河称“江”一事关系十分重大。
“工”字形的演变
“江”字由甲骨文到金文
“工”,象形字,像古代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曲尺。象形的“工”(图2)字在殷商晚期已经简化,把原来一端的方框形(图1、3)收缩为一横,同现代汉语写法已没有什么区别。在西周中期以前的金文中(图4、5),还能见到早期象形字的遗迹,即下底肥经过变化,最终也把下底简化为瘦笔单横。战国古文有在中竖右侧加“乡”形饰笔的形式,汉隶有故意把中竖写成“彡”形曲笔的形式,后代都有效仿。《说文》:“工,象人有规矩也。”本义应该是矩,即曲尺,但这一意义早已失落,后代用的都是引申义较早较直接的引申义是工匠。
江,属于疆域地区所有的水道,字形辨析:江字从水从畺,“畺”即“边疆”、“疆土”、“国家”之义,与文献上提到的边疆、疆土、国家的“疆”之“畺”同音(“边疆”就是“属于国家所有”的意思,其领头者称为“共工氏”。
“江”是形声字,从水工声,古读音是古双切,右边是水旁,左边是工,是声旁,古音里,“工”与“江”的读音差不多,都发gang音。现在还可以从有些方言里体现出来,如广东粤语里的“工”(gang)、在安徽省长江区域的姓氏中“江”(gang)等。
从以上解读中,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上古时期的“共工”世代处“江水”的缘故,于是上古时期就以其名字代称沭河,将其称之为共工的“工”(gang),后来加水字旁演变为“江”?
三、沭水(沭河)名字的时代
以上所述沭河名字变化的史实是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夏商时期,记载在《山海经》、《汤诰》等上古文献中。从西周开始,沭河之“沭”名见诸史册。
沭河之“沭”名,最早见于记载西周制度礼制的《周礼.职方》 ;其次见于东汉《汉书. 地理志》; 集中系统记载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沭水》。
《周礼.职方》载:正东曰 青州, “其浸沂沭。”意思是:正东地区是青州,那里有沂河和沭河可供灌溉田地。沭水,古人又写作“术水”,《汉书·地理志》:“术水南至下邳入泗。”唐代颜师古注:“术水即沭水也。”《水经注.沭水》载:“沭水出琅邪东莞县西北山。……又南径东海厚丘县……分为二渎,一渎西南出,今无水,世谓之枯沭;一渎南径建陵县故城东,……又南径建陵山西……南入淮阳宿预县注泗水。”。南朝·梁·顾野王所著字书《玉篇·水部》:氵术水,在琅琊,任绪钓鱼处。”这就是说,南北朝之前,“沭”字的异体字还有“术”、“ 氵术”等写法。
即是说,沭河的名字始于西周时期,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虽然较于沂、沭河形成的一亿三千多万年前的中生代晚期来说,三千多年无足道也,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足够书写一番的。
对“沭”的命名,一位微信名为“沂蒙匹夫”的作者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沭河的名字可能来源于《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炎黄五帝时期的一位名为“术器”的历史人物,笔者十分赞同它的观点。上文中《山海经·海内经》已经引用:“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
西周代商后,并不是周承商制,而是除旧立新,“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一词就出自西周,可见其“革新”力度之大。由此,将商代以共工名字代称的“江”改为的他儿子“术器”的名字,以“术”代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自此,开启了沭河名字的时代。
(作者 陈青)